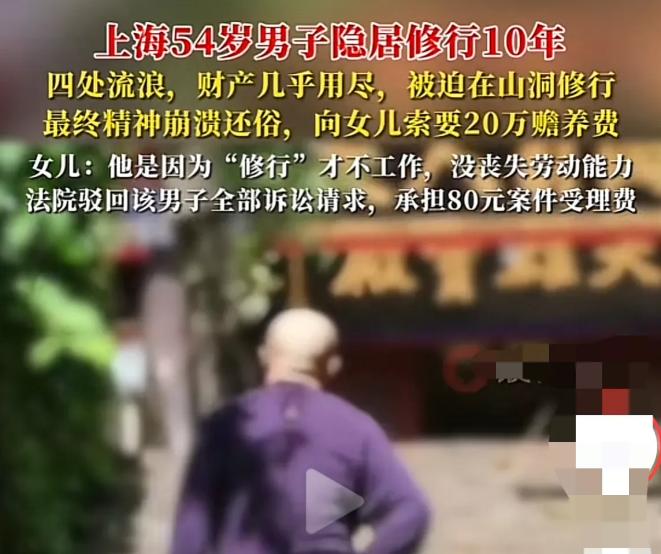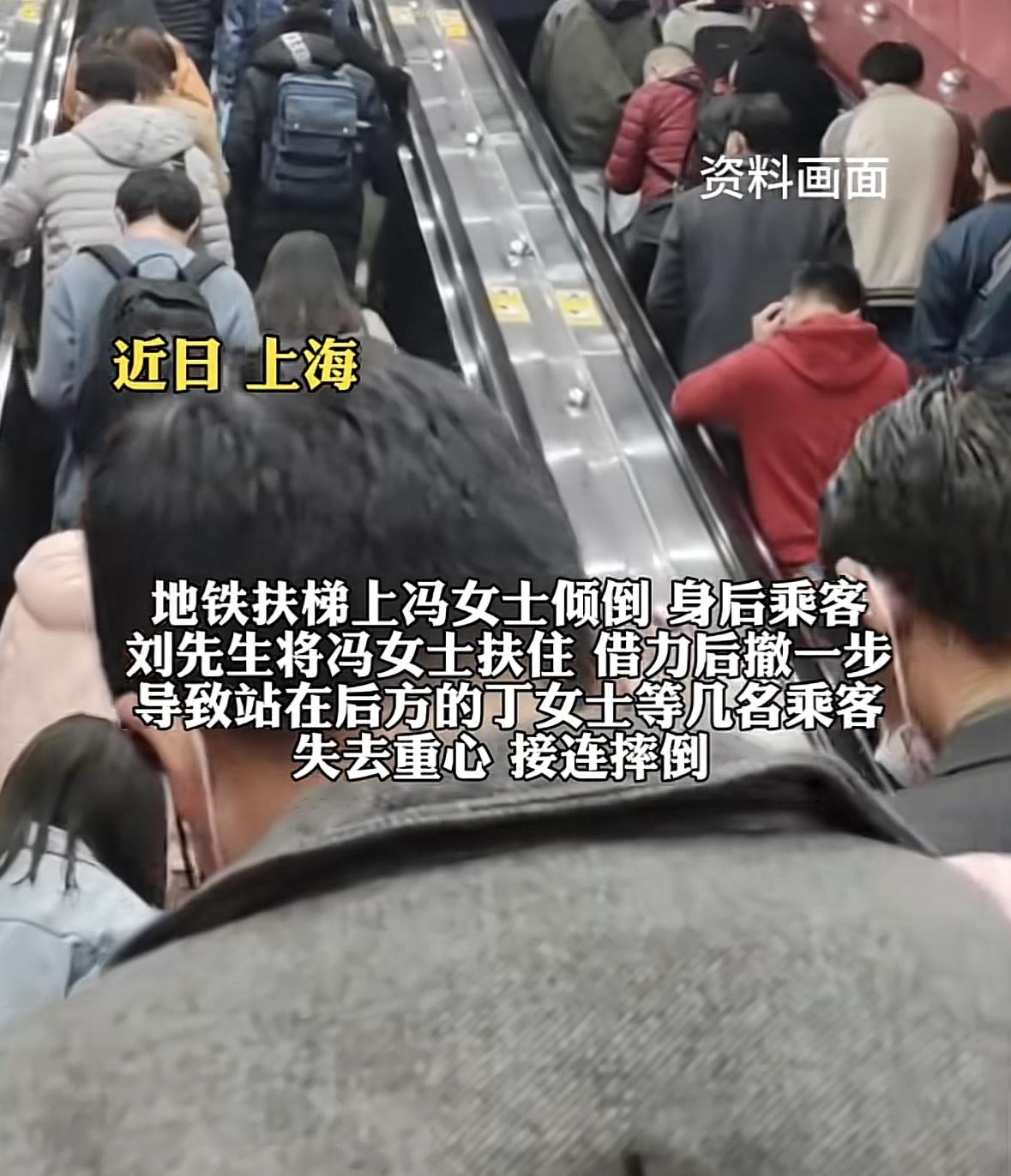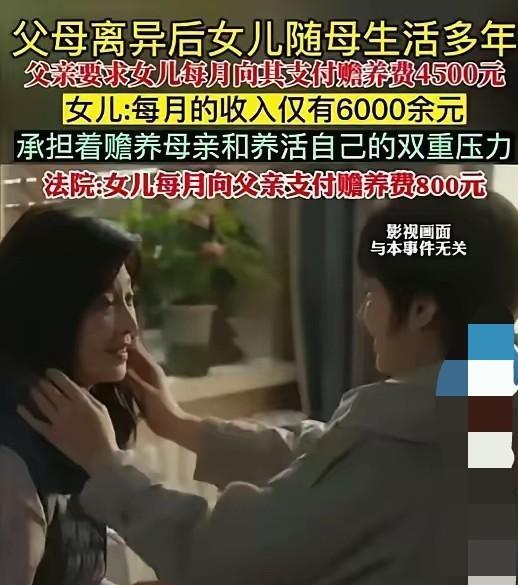在上海,一名54岁的男子张某因不堪工作压力,毅然辞去工作选择出家修行。这一决
在上海,一名54岁的男子张某因不堪工作压力,毅然辞去工作选择出家修行。这一决定不仅让他与妻子的婚姻走向尽头,更在十年后引发了一场与女儿的赡养纠纷。当张某耗尽积蓄被迫还俗,一纸诉状将女儿告上法庭,索要20万元一次性赡养费,法院的判决结果不仅理清了法律责任,更折射出家庭伦理与现实困境的复杂交织。据法院卷宗记载,2013年,时年54岁的张某在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担任中层管理职务。长期的业绩考核压力、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身心俱疲,用他在庭审中的话说,“每天睁开眼就像背着千斤重担”。在一次严重的失眠后,张某偶然接触到佛教典籍,萌生了出家修行的念头。这一想法遭到了妻子刘女士的强烈反对。“女儿刚上大学,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,他怎么能说走就走?”刘女士在调解记录中表示,她多次劝说丈夫正视生活压力,但张某去意已决。2013年秋天,张某办理了辞职手续,与刘女士签订离婚协议——协议中约定女儿由刘女士抚养,张某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抚养费,双方从此再无经济纠葛。随后,张某前往浙江一座寺庙剃度出家,法号“慧明”。起初几年,他靠着变卖个人物品和积蓄维持修行生活,与家人几乎断绝联系。女儿张婷(化名)在大学期间曾试图联系父亲,却只收到寺庙住持转达的“潜心修行,勿要打扰”的回复,父女关系逐渐疏远。十年间,张某在寺庙过着晨钟暮鼓的生活,每日诵经、劳作,看似摆脱了世俗烦恼。但随着年龄增长,他的身体逐渐出现问题,需要药物维持,而带来的积蓄在2023年初彻底耗尽。寺庙虽提供基本食宿,却无力承担其医疗开销,住持建议他“回归俗世,妥善安排晚年”。2023年夏天,64岁的张某褪去僧袍,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。此时的他身无分文,租住于城中村的一间小阁楼,靠打零工勉强糊口。一次突发胃病住院后,张某意识到自己无力应对未来的生活和医疗支出,想到了已经工作多年的女儿张婷。据张婷回忆,父亲找到她时,她既惊讶又陌生。“他说自己没钱了,让我负责他以后的生活。”张婷表示,父亲出家十年间从未尽过抚养义务,自己与母亲相依为命,如今刚成家立业,经济压力也很大,只能每月支付少量生活费。双方协商无果后,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女儿一次性支付20万元赡养费。法院审理过程中,围绕“子女对出家父母是否负有赡养义务”展开了激烈辩论。张某的代理人认为,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,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,这一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状况或生活选择而免除,张某年事已高且无经济来源,女儿理应承担赡养责任。张婷的律师则提出,张某在女儿成年前主动放弃抚养义务,离婚时已将财产全部留给母女作为补偿,且十年间未与女儿联系,如今突然索要大额赡养费有失公允。张婷提交了自己的收入证明、房贷合同等证据,证明其经济能力有限。承办法官走访了张某曾修行的寺庙和社区,了解到张某确实无固定收入和居所,且患有慢性疾病。法院认为,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,不因父母过去的行为而完全免除,但需考虑子女的实际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。张某要求一次性支付20万元缺乏合理性,应按月支付。最终,法院作出一审判决:张婷每月向张某支付赡养费1500元,直至其终老;驳回张某要求一次性支付20万元的诉讼请求。判决书中特别指出,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经济供养,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,鼓励双方修复父女关系。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对“赡养义务边界”的讨论。法律专家指出,父母的抚养义务与子女的赡养义务并非简单的等价交换,而是基于血缘的法定义务,但在司法实践中会综合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,实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。对于张某而言,这场诉讼或许不仅是为了经济保障,更像是一次对亲情的重新求索,而这段断裂十年的父女关系,能否在法律框架下得到修复,仍需时间给出答案。